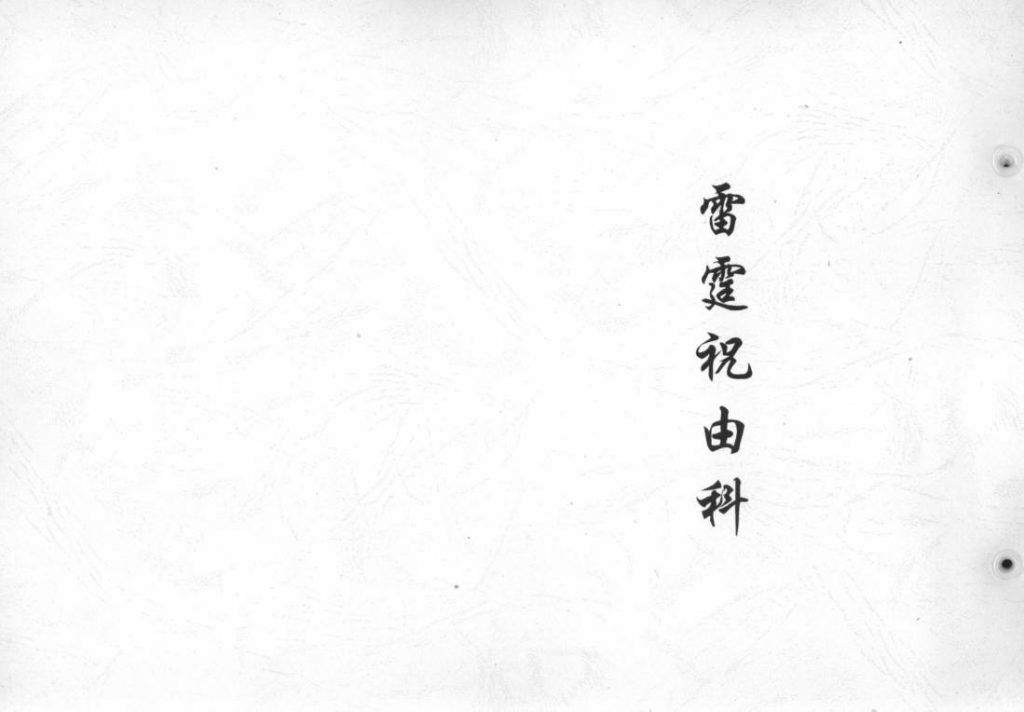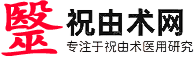我家二伯父,俗名范金钰(1916~2004),莆田市涵江区庄边镇前埔村人。据族谱记载:“自幼(9岁)入佛门,受佛戒,佛号释真空。(解放初)在破除迷信的浪潮中还俗,号书祥,从事fo事为生”[1]。他从小聪明好学,悟性颇高,年轻时已在莆田佛教界崭露头角。同时,因出身贫农,深受革命影响,1936年参加红军,1944年在中共闽中游击队司令部的辖区大洋大雾寺任住持,一直以fo事和治病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出生入死。解放后还俗回家,因精通佛法,在莆田山区佛教界德高望重。同时,他生前每年都受到省人民政府的亲切慰问。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少时,正值“文革”期间,有一天我母亲从田里劳动回来,右下肢突然红肿热痛,不能忍受,大伯虽然行医,但远在庄边卫生院。那天正值大雨滂沱,那时老家还是山间羊肠小道,要把母亲送到卫生院看病却是难事。母亲叫我把二伯叫来治病,二伯到我家后,嘱我们一家人不要声张,他小心翼翼地展开砚台,叫我在砚台上磨墨,然后看了我母亲的脚说:“这是‘煞气’,可祛毒治疗。”他先用泡好的盐水,拿着山上的新鲜的松枝,在我母亲脚上蘸着,口中念着符咒。接着,拿起毛笔蘸着我磨好的墨汁,在我母亲痛肢处从上至下画符,自始至终口中念着不为人知的符咒,最后把符录贴在患腿上,然后就回去了。二伯的做法,岂不是迷信巫术之类的把戏,但母亲怎么会相信他呢?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至深夜我就没有听到母亲的呻吟声,我们也睡着了。第二天早晨,等我起床时,母亲已经起床煮饭,她的脚居然不痛了。若不是眼见为实,我肯定不会相信。之后,我曾好奇的问二伯,在那个年代,他摇头不语。
二伯父在我心目中总是有点神秘感。首先他一到晚上,总是生怕人家知道 ,悄无声息地挑上担子出发,拂晓前勿勿赶回生产队参加劳动。后来发现,原来他晚上是出去偷做fo事。其次,由于从小受fo门教育,慈悲为怀,善心善行,在缺医少药的山区,经常免费偷偷地用符录咒语给人治病。他的这种行为,在那破除迷信的年代,是要冒被批斗或劳改的危险,不知是何缘故,他安然无恙。后来,我渐渐发现二伯的治病涉及范围还较广,在当地颇有名气,虽然找他的看病的人缄口不言,以目相视,但都心知肚明。二伯的治病之术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
我成人之后,从事中医药工作,随着广泛涉猎各类医籍,我才恍然大悟,二伯的治病方法不是什么巫蛊之术,而是人类社会早期的一种治疗手段,其兴起于远古,这是一种师出有名的原始医术——祝由术。
祝由在我国出现很早,上古时期就有苗黎巫医苗父用祝由的方法治病的记载,曰:“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祝由术可能来源于中国南方楚地,并和火神关系密切[2]。目前我国古代保留资料完整的早期祝由文献主要有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竹简《五十二病方》、《杂禁方》等,其中《五十二病方》中有32条介绍祝由术的医方,占该书存方量的11.3%,反映了上古祝由术的面貌[3]。
夏商至汉代,祝由术空前发展,曾因治愈汉武帝的急病而轰动全国。魏晋以后,祝由术融入了道家方术与释家的咒禁法,如葛洪在其道家经典《抱朴子内篇·登涉》中记载了禹步的具体步骤,当时盛行于当世的还有fo家的《龙权咒法》。可见祝由术在道教与fo教之间生生不息。我二伯9岁入fo门,又升为住持,在fo门中学习并掌握祝由术也是理所当然的。早年他在寺门里就是一边弘法,一边治病,就是缘由于此。
而后隋唐时期流行于民间的祝由术渐被官方认可,成为历代医事制度规定的医学专科,巢元方录入《诸病源候论》中的“养生方”及“养生导引法”和孙思邈《千金翼方》中的“禁经”等,反映了经过发展、达到高峰时期的祝由术面貌。宋代设有金镞咒禁科,官版医药巨著《圣济总录》中收录有“符录门”,不仅论述祝由术,还载录了300多道符录,祝由一度成为国家的基础医学教育科目,足见当时祝由术的繁盛。金元时期还出现了正式命名的祝由科,治疗疮肿丹毒、金疮、乳痈、疟疾等病症。张子和《儒事亲门》中记载了祝由治疗疮肿丹毒、金疮等病证的方法。我想,我母亲当时的“煞气”脚痛应属疮肿丹毒一类,可见二伯治疗还是有据可依的。
明代时祝由开始衰落,处于主流医学的边缘,在官方医疗机构中有提及,而在民间较为流行。至清代吴鞠通在《医医病书》中探讨了祝由起效的原因,并提出了“凡治内伤者,必先祝由”的观点;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作“祝由验录”,以备“不能备药石”时使用;到清末期祝由渐渐湮没,并与巫术、法术沦为一流,渐变为迷信巫术藏身障目之所倚了。民国时期,讲究科学,反对迷信,祝由被斥为迷信,乏人问津。解放后,更列为迷信之列,属于“牛鬼蛇神”,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几近消亡。此时的二伯治病当然只能转入“地下活动”。
改革开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社会学家开始探讨祝由及祝由术,如1997年张素玲等在《洛阳师专学报》上的《从祝由看古代巫术的医疗作用》、2006年江雪华等刊载在《社会心理学杂志》上的《“祝由”的文化与心理分析内涵》等文章。至此,人们对祝由及祝由术的看法有所改变,在民间应用有点起色,并有人提倡运用在养生方面。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医学界率先发音,1988年登载在《湖南中医学院学报》上袁玮的《<五十二病方>祝由疗法浅析》,其后中医界探讨的文章有:《中医祝由的发展与现实意义》、《古术“祝由”的起源及心理学意义》、《“祝由”的内涵及在现代中医心理治疗中的意义》、《从祝由谈中医与心理学的关系》等。
祝由真的能治病吗?历代医家看法不一。扁鹊曰:“信巫不信医不治,巫岂可列之医科中哉?”明显持否定态度。清代著名医家吴鞠通云:“凡治内伤者,必先祝由,详告以病之所由来,使病人知之,而不敢再犯,……而后可以奏效如神。”他认为祝由是可以用来治疗疾病的。
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的《灵枢·贼风》提到了祝由治疗的病因,认识到某些疾病的成因与精神情志刺激导致的气血运行逆乱有关,久而久之,可能这些无意识的心理波动会引起躯体症状,状如鬼神所做。在古代“毒药未兴,针石未起”之时,通过“知百病之胜”及“病所从生”的祝由可以转移患者精神,调整患者的气机,使精神内守,达到祛病愈疾的治疗目的[4]。
《素问·移精变气论》篇中:“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巢元方《古代医家对使用祝由治疗“末病”和“已病”持肯定的态度。认为疾病在初期,可以通过祝由调畅气机,使疾病消弥于无形;若任其发展,纵使加之于“毒药(此处指药物)或针石”,其预后也将是“愈或不愈”。
古代的“祝由”疗法能否去其糟粕,用其精华,答案是肯定的。祝由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早期的治疗方法,完全可以与巫术迷信相区别,应抛弃传统祝由中巫师具有的沟通鬼神、通天达地的迷信成份,提炼出其中的精华部分加以运用与发扬,特别是医学心理学上的暗示治疗手段。祝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朴素的心理暗示、归因替代、意识疗法等心理学思想,其疗法包含心理治疗学的因素,能够产生心理抚慰作用,类似于“安慰剂效应”。有研究表明,35%的患者能从安慰剂治疗中获益,特别对患有精神抑制症的患者,其有效率高达80%。这正如美国名医特鲁多镌刻在纽约撒拉纳克湖畔的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对医学的局限做出真情而理性的诠释,也说明了心理抚慰的重要性。
现代社会的变化日新月异,社会压力、生活压力使人们的精神压力“水涨船高”,不良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等往往会诱发情志病,使社会心理疾病和患病率不断攀升,直接威胁人们的健康。而情志病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如现代医学研究也印证了异常情志与肿瘤发生的关系,1985年,外国学者首提C型人格,即癌症人格,其人格主要特点是不善表达与宣泄情绪,压抑自已,克制、宽容与退缩,易无助而感到绝望等,心神之变成了癌毒发生的始动和促进因素。针对“癌症性格”,传统情志疗法应运而生,调心神而防治癌瘤临床意义重大。
情志病更多的通常会触发一系列躯体器质和功能性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病、心脑血管疾病、胃肠功能紊乱、月经失调、癔病、神经性头痛、焦虑症、精神病等。同时,使用西药又有较多的副作用。而祝由的传统情志疗法,可谓是现代的精神支持和疏导疗法的雏形,包含着启迪当代心理治疗和心理分析的重要文化因素,同时,在中医史上又有丰富的治疗案例,如果能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治疗,使中西医在应对精神疾患方面取长补短,互相汲取养分,共同携手面对心理与精神疾患日益严重的现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这些都只是“纸上谈兵”,祝由及祝由术何去何从,不得而知。
随着二伯父的逝去,祝由术在莆田老家方圆一带,似已销声匿迹。想起我二伯父的音容笑貌以及给人治病的怪术——祝由术,我深情的呼唤,中国真正的祝由术——您在哪里?还好吗?有朝一日,让您重出“江湖”造福人类,您准备好了吗?
参考文献:
[1]范金绪.莆田广业里范氏族谱.2000:344
[2]李倩,颜红.古术“祝由”的起源及心理学意义[J].黑龙江中医药,2011(3):14~15.
[3]袁玮.《五十二病方》祝由疗法浅析[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8,8(1):38~40.
[4]王洪图.内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786~787.